编者按:去年的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委员会上,突然发生了关于海洋保护区是否与《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的第二条中的“养护包括合理利用”相违背的争论。为了回应这一争论,NGO找到了曾经参与上世纪七十年代《公约》谈判的骨灰级的专家Bob Hoffman, 请他回忆了下当年对这一条的谈判里程,以正本清源。下面就是老爷子写的文章。
《CAMLR公约》第二条的初衷
Bob Hofman博士
引言
近年来,CCAMLR成员国对于《CAMLR公约》第二条的理解有时似乎存在分歧。因此,旨在纪念公约签署35周年的CCAMLR研讨会有必要在其议题中提请就以下问题交换意见、达成共识:
Ÿ 平衡CCAMLR渔场的管理与生态系统方法、区域保护的执行;
Ÿ 提出“养护”一词的定义包括合理利用的公约第二条。
由于后文所述的原因,这两个议题似乎反映出各方对于公约的初衷及部分条款存在理解或解读上的偏差。关于上述第二个议题,“包括合理利用”这几个字的内涵在公约定稿时是各方都清楚理解的,因此现在对这几个字的理解也应与当时保持一致。也就是说,对公约涉及区域生物资源的“合理利用”指且仅指符合公约第二条第三款a、b、c三项所规定之原则的合理利用。
同样,上述第一个议题似乎也反映出各方对公约的初衷和相关的义务在理解或解读上存在偏差。公约第二条清楚地指出,生态系统方法是在公约所涉及的区域进行渔场管理及相关活动的必要基础;而区域保护则是公约第九条第二款g项专门提到的实现这一目的的途径。
背景:关于公约第二条的初衷与措辞
促成公约谈判的主要背景有两个:(1)人们担心如果不加以有效管理、任其按照预计速度发展的话,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南极磷虾捕捞业将破坏以磷虾为食的鲸类枯竭种群数量的恢复,并对以磷虾为基础的南大洋生态系统结构与运动产生不利影响;(2)人们逐渐认识到以单一物种的最大持续产量(MSY)这一概念为基础并不能对野生生物资源进行有效的管理。
因此,公约的出台就是要建立一套生态系统养护制度,而不是区域性的MSY渔场管理制度。公约明确提出的目标是确保捕捞及相关活动不对所捕捞的物种和种群及其支持或生态相关的物种和种群产生长期或不可逆转的负面影响,从而保护南极海洋生态系统的结构和运动。换言之,公约的目标是确保捕捞及相关活动不对南极海洋生态系统中各种生物组成部分(即鱼类、甲壳类动物、鸟类、海洋哺乳动物和底栖物种等)之间的生态学关系产生不利影响。
现在公约第一条和第二条所体现的生态系统方法是1978年初在堪培拉的第一轮谈判中得到原则性通过的。在1978年7月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第二轮谈判中,若干《南极条约》缔约国指出,公约第二条第一款中的“养护”(conservation)一词在其国内译作“保存”(preservation),因而堪培拉谈判形成的措辞在其国内可以解读为在公约区域禁止商业捕捞。实际上,公约的本意并不是要禁止捕捞,而是要确保捕捞不会产生与公约第二条第二款(当时)所列举的养护原则相悖的影响。
为了澄清商业捕捞在特定条件下也是可以进行的,相关方面提议并通过在公约第二条中额外加入一款——新的第二款,即“为本公约的目的,‘养护’一词包括合理利用。”对于第二条新的第二款中“包括合理利用”这几个字的理解在当时并不存在分歧,而现在也不应存在分歧。由此可见,虽然后来人们似乎认为应当在生态系统养护和渔场及区域管理之间取得某种程度上的“平衡”,公约中却并没有什么条文支持这一观点。因此,任何不符合公约第二条所明确规定的养护原则而对公约区域的生物资源加以利用的做法都构成“不合理利用”,这种利用是有悖公约初衷的。
关于另外一个相关的问题,在1978年7月的第二轮谈判中,若干缔约国指出当时(堪培拉谈判拟定的)公约第二条第二款的措辞没有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人们往往不一定能掌握足够的信息来提前确定目标物种和种群、依存物种和种群及相关物种和种群的最大净繁殖力水平,也不一定能及时找到必要的措施来防止出现不可逆的变化、保证后代可以选择的管理措施不致减少。认识到这一点后,有关各方提议并通过将后来第二条第三款a项的措辞从
“防止任何被捕捞种群的数量降低至最低净繁殖力水平以下”
改为
“防止任何被捕捞种群的数量低于能保证其稳定补充的水平,为此,其数量不应低于接近能保证年最大净增量的水平”。
同样,有关各方提议并通过将后来第二条第三款c项的措辞从
“防止海洋生态系统发生有可能在人类一个世代的时间内都难以逆转的变化”
改为
“考虑到目前捕捞对海洋生态系统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引进外来物种的影响、有关活动的影响、以及环境变化的影响方面的现有知识,要防止在近二三十年内(经谈判商定的人类一个世代的近似长度)南极海洋生态系统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或减少这种变化的风险,以可持续养护(即,不是产出)南极海洋生物资源。”(括号内的内容为作者添加)
后来成为公约第二条第三款b项的措辞未提出也未经过任何修改。因此,防止被捕捞种群数量下降也适用于依存及相关物种种群,而后者的最大净繁殖力水平可能明显高于捕捞的目标种群。
如果对于渔场及相关活动所产生的影响是否有悖于公约第二条的养护目标与原则不存在顾虑,即认为渔场及相关活动对公约区域生物多样性及生态学过程造成影响的风险为零,那么原本是可以不用进行特别区域管理的。然而,至少从某些渔场看来,它们对于目标物种和种群、依存物种和种群以及/或者生态相关物种和种群的影响很有可能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至少可以部分通过公约第九条第二款g项特别区域管理的方法来加以解决。比如,至少对于某些渔场来说,产卵季节禁止在产卵区域进行捕捞可能会改善捕捞对当地的长期可持续性所产生的影响。
同样,通过建立渔业保护区或研究性保护区,评估、监测和对比开放渔场与禁捕区(只允许进行有限研究性捕捞)在储量状况上的差别,我们可以降低过度捕捞的风险。另外,只有在若干进行过或可能进行捕捞的代表性区域实行禁渔、只允许开展相关的实验性捕捞和生态系统研究,我们才有可能将捕捞与气候变化的影响区分开。
总结
公约第二条第二款的加入只是为了澄清一个问题,即公约的出台并不是为了禁止捕捞及相关活动——只要这些活动在设计与执行上符合公约第二条第三款提出的养护原则。在1980年拟定和签署公约时,各方对这一点的理解都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公约第二条的措辞并不存在歧义。同时,第二条也明确指出公约区域的渔场及相关活动的管理须以生态系统养护为基础。另外,公约第九条第二款g项明确指出区域保护是实行生态系统养护的有效措施之一。因此,过去、现在都没有理由在生态系统方法、区域保护与CCAMLR渔场的管理之间进行所谓的“平衡”。也就是说,区域管理和渔场管理本来就是互补的,是为实现公约第一条和第二条所提出的生态系统养护而服务的。
译者:范筱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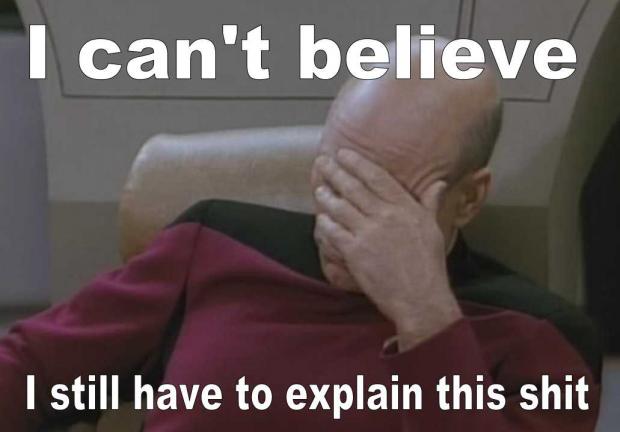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